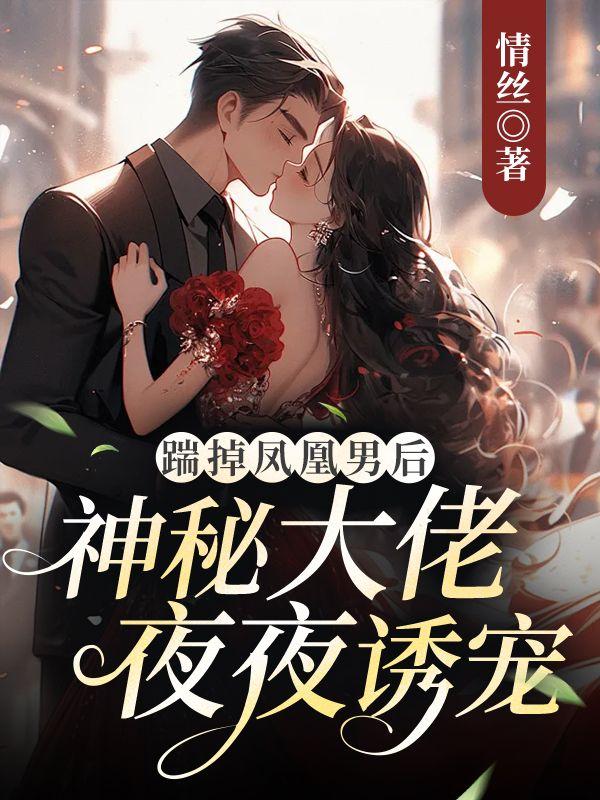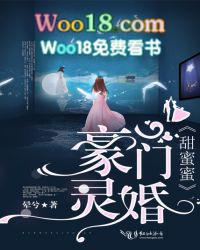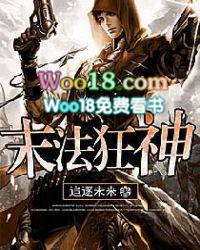阁笔趣>都重生了谁还做演员啊 > 第398章 盘古堆建成(第2页)
第398章 盘古堆建成(第2页)
身穿白色洁净服的焊工,操作着磁力约束下的真空电子束焊枪,在氩气保护氛围中,焊束无声地刺入金属接缝。
每一条焊缝的长度都足以绕行基地一周,而厚度容差要求精确到微米级别——这是一个不允许任何“沙眼”或“虚焊”的世界。
洛珞的身影数次出现在安装平台旁的监控室,目光透过观察窗,扫过实时回传的红外热成像图谱,监测着焊接热影响区是否均匀,任何微小的温度异常都可能预示着潜在的应力集中点。
漫长的焊接与冷却程序结束后,立刻被连接到庞大的真空抽气系统。
分子泵、涡轮泵、离子泵齐声嗡鸣,接下来是更为严苛的真空密封性能测试,将杜瓦内部气压降至宇宙深空般的极低值。
高灵敏度氦质谱检漏仪如同最忠诚的猎犬,沿着每一道焊缝、每一个法兰接口一寸寸“嗅探”。
任何微小的氦气示踪分子泄漏,都会立刻在仪器上激起警报般的尖峰。
这个环节耗费的时间超出了所有初设预案,整整两周在反反复复的补焊、再抽真空、再检测中流逝。
王世峰每天清晨带着熬夜的黑眼圈向洛珞汇报进展:
“A区二次复检通过,漏率优于10-9Pa·ms标准,B区接头重新处理,正在进行48小时稳定性测试……”
洛珞的回应总是简洁有力:
“好,标准就是标准,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不需要差不多。”
他深知,任何微小的泄漏在未来的超高温度场和强辐射环境下,都将成为灾难性的阿喀琉斯之踵。
但这还不够。
真正的考验是“找漏”。
氦质谱检漏仪被部署在杜瓦容器外壁上最重要的接缝、法兰接口和焊缝处。
技术员们手持氦喷枪,小心翼翼地将微量的氦气“探针”喷洒在可疑位置。
氦是宇宙中穿透性极强的惰性元素,若有任何比针眼还小千万倍的泄漏点,氦分子便会渗透进去。
内部的氦质谱检漏仪核心探测器会立刻捕捉到这极其微弱的信号,发出尖锐的警报,并在屏幕上精确显示出泄漏点的位置坐标。
每一次警报响起,都意味着一次失败的焊接或密封,需要立刻标注、记录、打磨、再焊接、再抽真空……两周的时间里,王世峰副总工程师几乎扎根在现场,向总设计师洛珞日复一日地汇报着这场“捕风捉影”战争的进展:
“B7区法兰密封圈复检通过”、“主焊缝Q11段二次补焊后氦峰消失”、“整体静态真空维持度已稳定达标……”
与此同时,超导磁体系统进入了最关键的预冷与调试阶段。
环绕在杜瓦核心外围的,是——庞大的超导磁体系统。
这些由特殊合金线材缠绕的巨型线圈,将在低温超导状态下产生强大而稳定的磁场,约束住聚变反应中高达上亿度的等离子体。
此刻,它们正在进行启动前的关键预演——预冷与通电调试。
巨型低温冷屏组件内部,液氦冷却回路如同血管般被激活,液氦在特制管道中奔流。
低温传感器报告着每一个冷屏单元的温度稳定地向绝对零度靠拢。
工程师们严密监控着温度梯度的变化,防止急剧的温度变化导致材料收缩不均产生不可逆的应力。
冷却过程是缓慢而精确的,每一步都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洛珞在主控中心的屏幕前,关注着代表磁体线圈状态的数据流:
电阻是否完全归零?磁场梯度是否均匀?冷却剂流量是否精确匹配计算模型?
任何一丝微小的异常波动都逃不过他那被【头脑风暴】赋能过的超强计算力和近乎直觉的物理感知。
他深知,超导磁体一旦失超,不仅意味着磁场的瞬间崩溃,更可能因巨大的能量释放造成灾难性破坏。
每一个数据的平稳过渡,都预示着这条个庞然大物正在安全、有效地苏醒。
庞大且复杂的激光阵列系统,同样在进行着最精密的校准与能量通道联调。
巨大的高功率激光束将从阵列的四面八方聚焦于杜瓦核心内的靶丸“龙睛”。
高能激光束在模拟腔内往返穿梭,束斑稳定性、靶点聚焦精度、各子束路的同步延迟被调校到了皮秒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