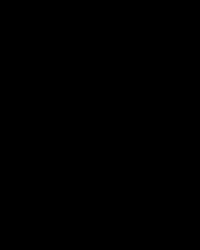阁笔趣>如何溺毙一只鹤 > 第一百五十八章 瓦解冰消(第3页)
第一百五十八章 瓦解冰消(第3页)
“将军夜台衰草生。”
“昶王总以为这句话野心太盛,激起他父皇的疑心了。可他到死也不知,这将军在他父皇眼里,指的是你父亲,安虞将军,贺柏。”
贺言吞了口口水。
秋茶道:“沈文与莫潮做的局并不十足周密,盐槽失案当年就疑点重重。可是,定宁帝在这种情况下依旧灭了宋家满门。你知道他为何这么着急,宁可错杀不肯放过吗?”
贺言摇头。纪清急促地吸进一口气。
秋茶缓缓地说:“因为宋家不仅涉嫌勾结乌月,又与边防相关。他害怕,乌月会把他们当年的交易捅出去。他在灭口。”
贺言哑口无言。纪清目瞪口呆。
秋茶淡淡地说:“你父亲,茯苓,或者柳娥,他们有没有和你讲过,你一定要在一个春日,去一次雁北。”
“是时春草刚生,尤其下过雨后,登到最高的楼台上,抬起手就能摸到卷着江水湿气的东风。空气里满是翠色的味道。真的是翠色,你能闻出春的颜色。”
“我之后再没见过那种连绵至天角的旷野,还有其上长得极高的天空。灯红酒绿也好,纸醉金迷也罢,都不及雁北的草原,牛羊和夜空。”
这时侍卫在门外喊道:“贺大人,您和犯人已经会面太长时间了,传出去恐怕有损声誉啊!”
秋茶抬眼看了一眼门外的光亮,道:“我犯的罪够多了,落得今日这结局,并不冤枉。”
贺言的表情由痛苦变成了难以置信,竟显露出几分孩童般的天真:“真正该死的人却高居于庙堂之上,凭什么。。。。。。凭什么?”
“世上没那么多凭什么。”秋茶推了他一把,“走吧——”
贺言起身。
秋茶盯着他玄色袍角上的金纹,这些纹路翻腾着向上,缠绕着青年的腰身,又在胸前化成一只鹤。她不由忆起她印象中的那个贺家。
那时候她还是小姑娘,头上顶着两个团子,卧在长姐怀里。大孩子们有自己的话要说,她听不懂,只静静地看着他们。贺柏弱冠年纪,正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左右是他的副官,舜吾和柳祈,这两人身旁分别是舜英与柳娥,他们各自的族亲。
所有人都众星捧月地围着贺柏,指点江山,谈笑风生。青年们笑着闹着,叫久春,久春哥,贺久春。她长姐更有分寸,用的是另一个称呼——
“——少主。”
秋茶的嘴唇缓缓开合,说出那个几十年不再用过的词。她们曾这么唤青年贺柏,她临死之前又这般唤他的儿子。
“我。。。。。。”贺言抹开一把眼泪,“我不是。。。。。。”
秋茶想,等到明日她死了,这群人就都不在人世了。若在九泉之下重逢,她有何颜面去见故友呢?
贺言拂袖离去。屋外的寒风椎刺刀削一般刮过面庞,泪水淹过的地方很疼。
纪清躲在暗处,看着贺言上马。
他在心里琢磨着怎么安慰贺言:贺言一定会把脸埋在他肩颈处,喘不过气一般一抽一抽地哭。他会学着贺言少年时安慰他的模样把手放到贺言颈后背后,有一下没一下地顺。
他登基后,即使不能将此事昭告天下,也一定会想办法改一改史官对雁北的记述。
但出乎纪清意料的是,贺言没有回府,而是往城门的方向。
他还要见谁?纪清心里嘀咕,跟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