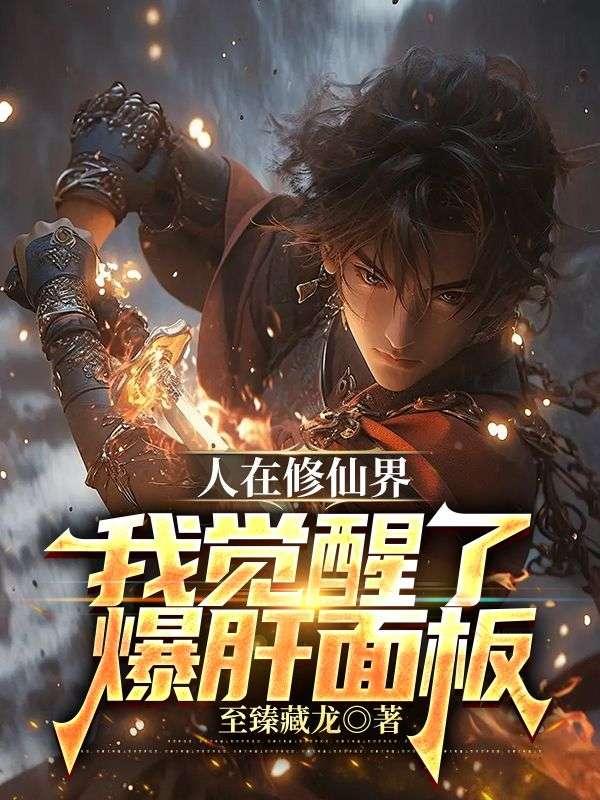阁笔趣>如何溺毙一只鹤 > 伪结局 春来苦寒(第2页)
伪结局 春来苦寒(第2页)
纪清听见了,溪水的声音像风吹过风铃,又像是孩童的欢歌。
贺言笑着看他,笑得极张扬极放肆,衬着朝阳耀世,山川同光。他的眉眼间淌过十古的云舒又卷,唇角开尽了九州的荼蘼长醉。
“是有水声。”纪清说,“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贺言兴高采烈地重复了一遍。
纪清从不是个扫兴的人,除非他刻意这么做。他下马,向贺言伸出手。
“你要做什么?”贺言问着,扶着他的手跳下来。
贺言在下马的一瞬间被纪清吻上双唇。
这个吻很急,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两种花香汇聚在一起,贺言再一次品尝到了那种涩味。他来不及问,男人只是饥渴地摄取他的津液,连咬带啃。
贺言的舌头全然顺从纪清的搅动,他被亲得眼前发晕,迷糊着,几乎被一个吻带入高潮。纪清好像舔舐开他的一切,从唇舌到魂魄。吐息间的热气打在肌肤上,像是蒸腾而上的云。
他背后是雁城,身处高处,面前只有无尽的天空。
贺言胃中抽动,四肢和躯干都僵硬了,只能瘫软在纪清怀中,全靠那双手支撑着。这人明明瘦了,力气却更大了,像一双巨钳束缚着他。这种痛感让他很安心。
纪清边亲边把手往里摸。
“。。。。。。呃、不行!唔。。。。。。”贺言在喘息的间隙艰难地说。
纪清置若罔闻,把修长的手指探进层层叠叠的衣襟,最后在几层衣服之后,摸到了贺言胸口滚烫的肌肤。
贺言想要把他推开,想要结束这个吻。但纪清咬着他的舌头,把他囚禁在一处。
纪清终于摸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条项链。他拽住那只耳饰,往下轻轻一拉,红绳便断了。他把这耳饰紧紧握在手中,放开了贺言。
贺言满脸通红地整理衣襟,嗔道:“青天白日的,还是在外面。。。。。。”
纪清没头没尾地问:“你最喜欢的季节,是春天还是冬天?”
贺言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安元帝生性多疑,为我开府无疑于监视,你我疏于见面,整整七年。五年前他死于纪辰之手,先帝继位。先帝放松了对我的控制,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明目张胆地与你并肩。”
“那是一个春天。所以我喜欢春天。你我第一次见面却是盛夏季节,骤雨狂风。你深知我多想,这个季节不必多言。秋季很平庸,而我们在一起的那日下了初雪。我忘不了那个冬天,雪飘飘扬扬,落在你身上如鹤羽一般,你告诉我,我爱你。”
贺言笑了笑:“是,我也爱你。”
“我想了很多要说的话,该从何谈起呢?你读过那么多话本,有多少结局是真正合你心意的呢?”纪清轻轻按住了心口,有微小的、纸张的脆声传出。
“究竟要怎样的结局才配得上你我种种,究竟要去何处才能让你铭心刻骨?后来我又想,天地浩淼而生蜉蝣,到底要多少只蜉蝣才赶得上天地的变化?是无尽的。”
贺言挑眉:“你想说什么?”
“正因我要利用你,才会救你。正因你要利用我,才会给我救你的机会。这是没有错的,你我都没有。最稳固的关系是利益关系,若将利用贯穿到底,倒也不会杂生旁枝。错的是这之外的情感,比如愧疚,比如爱。”
纪清向后撒了两步,石子随着他的动作滚落,撞击在裸露的乱石上,明明声音微不可查,却清晰地落进纪清的耳朵里。
“你要做什么?”贺言终于警觉起来,“你说过要和我一起走的。”
“你更喜欢春天还是冬天并不重要了。”
两行清泪款款而下,经过他扬着笑的角。纪清张开双臂,袍角似白鸟般飞舞。
春风扬过二人交汇目光中的尘埃,堵塞住贺言的话语。
贺言忽的意识到什么,心口一冷,朝纪清奔去。他长长伸出手,妄图要抓住他。
纪清轻柔地说:“以后看见春花,看见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