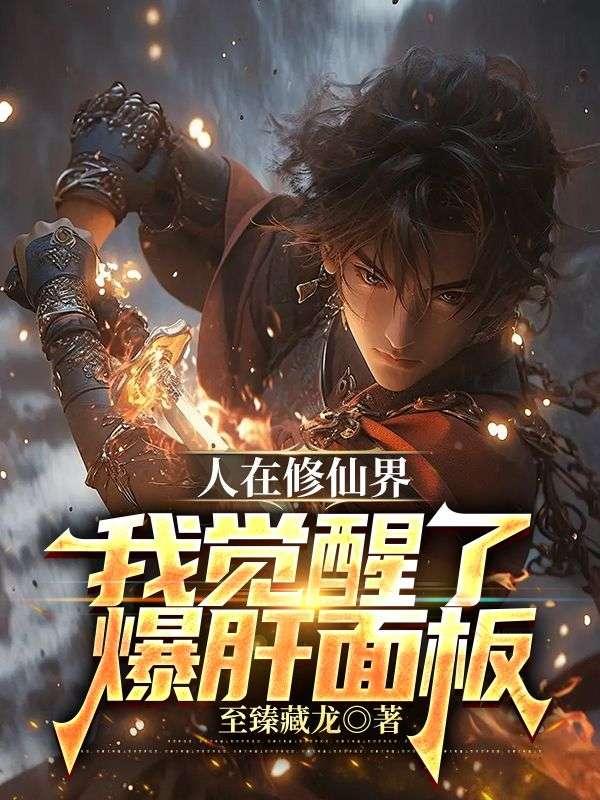阁笔趣>如何溺毙一只鹤 > 真结局 下一个春天(第3页)
真结局 下一个春天(第3页)
贺言并不知纪清的这些抱怨,径自洗浴去了。
听着水声,禁欲已久的鬼王爷颇不适。情欲和爱意是可以分得彻彻底底的两样东西,在宫中那一夜他不照样上了他么?
纪清咬着牙等贺言出来,只见这人从衣柜角落里取出一件牛皮包好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打开,捧在怀里,才把自己团成一团缩在床角。
纪清认出来了,是他的衣服。
他嗤笑,贺言竟然留着“利用对象”的遗物这么多年,也不怕勾得鬼怪上身。摆出一副长情的样子做给谁看?纪烛,贾昀尧还是莫习卿?知道他们两个那点破事的人还有几个活着?
床脚传来窸窣声和闷哼声,纪清青筋直跳。
他必须承认贺言是个正常男人,有情欲也是正常,但用死人的衣服。。。。。。实在是让鬼王爷难以接受。
纪清走到床边,冷脸凝视着这场变态的情事,问道:【你不是骗过我吗?】
贺言自然听不见。喘息声渐渐轻了,哭声压过来,像一只压抑的小兽。纪清听见这人啜泣道:“纪洵川。。。。。。放过我吧。。。。。。”
纪清挑了挑眉,把手放到腰腹的伤疤处,道:【不可能。】
3。
贺望离开后将军府变得十分空寂,鬼比人占的屋子更大。纪清开始监视贺言的生活,但很快感到无趣。
贺言话很少,日日低头做事。他连话本都不看了,无事时要么在草场上沉思要么打盹。有人设宴他也会去,谈笑风生,也不知笑得几分真几分假。
那日宴上他似乎喝多了,被几个副官架着回府。纪清幽幽地跟在后面。贺言要酒疯很厉害,纪清早就见识过了。他非要把席上的桃酥包好带回去,副官说次日现做现吃吧,不然撂一夜品相就不好了。
贺言拧劲上来了,一定要今夜这些,怎么劝都不听。
“有人要吃,今夜就要。”他说,“不是我要吃。”
酒劲上来就是这样。副官们互相安慰。毕竟将军府也没其他人了。
纪清看了看那桃酥,是他爱吃的那种没错。
贺言被灌了醒酒汤,放到床上。纪清不想让旁人进贺言的卧房,但也不能把贺言扔到街上。他扯扯那些人的衣带,就当做惩罚了。
贺言咳得很厉害,能把房顶震起来一般。纪清给他倒了杯水,反正贺言现在半梦半醒,不会生疑的。纪清把杯子放到床头,再去夺贺言的被子,试图让他醒过来。
贺言无意识地把被子往自己怀里团,哼哼着,昏迷得更沉了他们当年同床共枕时,也是这样抢被子的。
贺言可能会醒,然后踹他一脚,抱怨两句,再睡去。这时候可以把他揽进怀里巴手指插入他的发梢,或者吻他的耳垂。
但即刻,那些争执与怒火又占据了回忆的中心。
纪清的神色冷下来:【你真的爱我吗?】
贺言沉沉睡去。他的皮肤不再光滑,变得斑驳。
雁北的苦寒养不出荼蘼花,圆日与狂风里骏马的嘶鸣会盖过金玉相撞的脆响,那副玲珑心肠被砂石磨得粗糙。
纪清挨着他躺下,知道他不会回答了。
虽然是孤魂野鬼,但纪清依旧无处可去。他只这样“陪”着贺言,“惩罚”每一个靠近贺言的人。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变成鬼之后也离不开他。
年少时的悸动再未在纪清心中出现,他想他的陪伴不是出于爱,他不再爱他了。
这些年里,贺言一次也没有祭奠他。除了那些释放欲望的夜晚之外,贺言的人生中没有他的任何痕迹。他的名字只在静谧中伴着哭声被吐出,贺言幽幽地哭,暗暗地落泪,不知道是在哭谁。
是把他放在心底,还是遗忘了?纪清愤愤不已。但贺言也未寻新欢。可能一次失败的爱情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少年意气,对女人他下不去手,对男人他心有千结。
自打清延十二年之后,贺言四十岁,身子走上下坡路。对于他这种常年练武者很少见,但他心病难医,积郁成疾。最开始是咳喘,后来嗜睡、心悸。贺言试图在贺望面前掩饰,这孩子没心没肺刚好看不出来。
纪清心说也好,没心没肺总比狼心狗肺强。
4。
贺言最后大病一场,医师说可能不妙。贺言并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悲哀,他只是笑了笑,说声谢过。
之后贺言前往雁城。纪清不能理解,“雁北的将军要死在雁北”,从贺柏到贺镜,每个人都践行着这句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