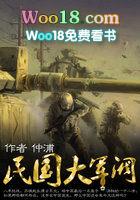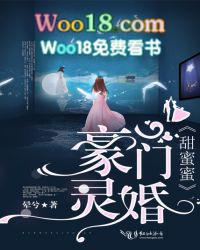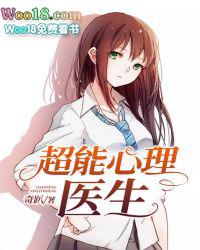阁笔趣>我画的人都死了(探案) > 第二十二章(第2页)
第二十二章(第2页)
“草民匡嘉德见过大人。”
崔衍点点头:“不必多礼,想来你有消息要说。”
匡嘉德站着有些拘谨。
“大人,草民认得告示上所画之人。此人名唤廖光远,今年二十八岁,剑南道人,九年前考中举人,于是来京城参加春闱,两次不第,耗时六年铩羽而归。”
“我与他道中相识,相互照应,一直交好。当年我们约定今年再考,不知怎么没有见到他,我还以为他许是暂时不考了,没想到在告示看到他,也不知是何事……说来,廖弟为人古道热肠,还曾对我有恩。”
果然,如崔衍所料。
他下意识寻找姜渝的目光,果不其然姜渝也在看他,两人对视一眼,默契一笑。
不过崔衍还要仔细盘问匡嘉德,于是这笑转瞬即逝,转头面向匡嘉德时瞬间严肃。
“小霍,都记下来了么?”崔衍发声询问。
坐在一旁小案上的年轻小吏连忙应是:“都记下来了大人!”
“好,匡嘉德,将你与廖光远相识和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事一一如实道来。”
匡嘉德拱手应是。
六年前,距离京城五十里的路上。
二十七岁的匡嘉德背着沉重的竹制书笈,腰间一把乡亲所赠的短剑,一手扶着头上草枝翘起的斗笠,一手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病驴,粗糙皮靴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因为下雨而泥泞不堪的道路上。
“好冷啊,这雨下了三天了,怎么就是不停?”他将扶斗笠的手短暂放下来放到口边吹气,试图让僵硬的手得到一些缓解。
此时正是冬季,而京城左右却是一反常态淫雨霏霏。
这就苦了像匡嘉德这样的赶考人,他被冻得瑟瑟发抖,晚上烧着火都睡不着,现在放在外层的粮食也被一刻不停地雨水尽数打湿。
那些干粮都是自家面粉做的馍,是爹娘在他出发前夜用粗糙的手一块块包好给他带上的。
都被雨水打湿,馍被浸透后从包裹里流出乳白的水。
匡嘉德补救的时候已经晚了,馍水流的到处都是。
他心疼的看着软烂的馍,用手小心翼翼心痛的捧着拢着聚到一块儿。
他想起了家乡勤劳一辈子苍老佝偻,却还要弓着腰奋力举起锄头凿向并不丰饶土地只为养活他们一家人换取生活的爹,还有早起晚睡,一天到晚缝衣补鞋,做饭带孩子的娘。
这些馍是爹一滴滴汗水浇灌出来,娘精打细算从家里七口人口中一点点省出来的,他不孝,没什么本事,二十七岁才考上举人,耗尽了家中钱财,才有资格来到京城。
爹娘的期许,兄弟姊妹的期许,乡亲的期许——好重好重。
他不能失败,他一定要出头!
将混着雨水潮味的馍拼命往嘴里塞,匡嘉德吃的狼狈而绝望。
接下来路愈加难走,他艰难行进。
直到脚下一滑被书笈的重量带着重重摔在地上,手中绳子脱手,病驴受惊跑走,斗笠掉下山崖,书本被褥散落而出。
匡嘉德绝望的喊着驴,但驴跑的很快,不久消失在路的尽头。
雨淅淅沥沥,打湿匡嘉德单薄的夹棉衣袍,沉重而寒凉。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岂能轻弹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