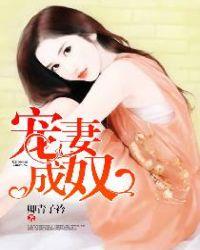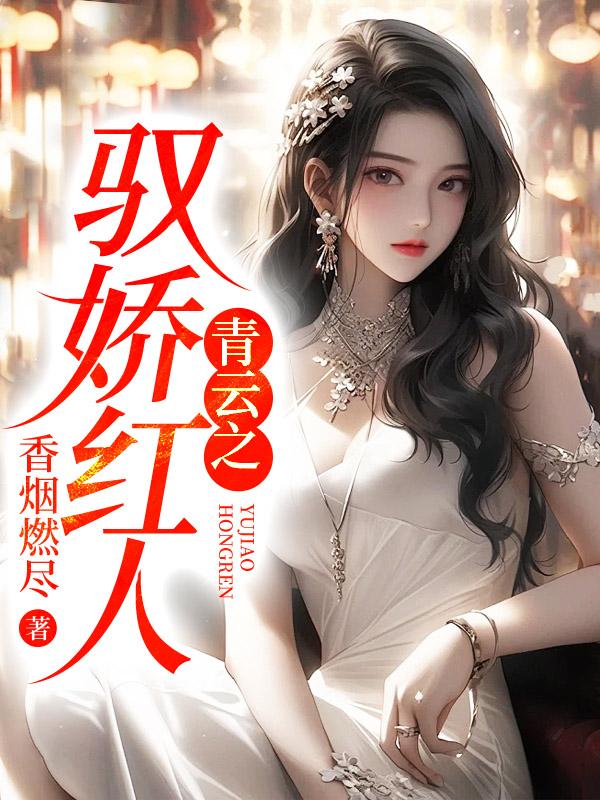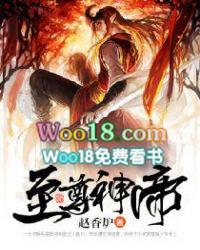阁笔趣>[三国]“病弱”谋士,战绩可查 > 8090(第17页)
8090(第17页)
斜阳照落,在素色营帐上落下红晕,如若一个面红耳赤的看客。
同一时刻,远在豫州的张绣走进营帐,在一男子身边坐下。
“文和,曹操率领大军南下,似要征讨豫州。我们可要正面迎战?”
他身旁的男子正是谋士贾诩。贾诩貌不惊人,行止平和,谁都想不到,正是此人在长安搅出大乱,不仅让夺取大权的司徒王允身首异处,还让李傕、郭汜充当开路的利刃,白忙活一场。
听了张绣的询问,贾诩没有开口,只是在沙地上写下了一个字。
——等。
第87章孙策周瑜孙、张结盟。
张绣不知道贾诩要他等什么。
他的叔父对贾诩极其钦佩,张绣即便有着不同的想法,也只能将所有质疑压在心中,装出一副信服的模样。
如果只谈论近两个月的成果,他对贾诩确实是有些信服的。
与李傕、郭汜决裂后带着他们全身而退,智取南阳,占据豫州,与陈王等人达成协议……
一桩桩,一件件,至今为止还未出过差错。此人的眼光与计谋,的确非凡。
张绣听从贾诩的话,格外耐心地等着。他等到三天后,曹仁率领青州兵包围阳安,五天后,临近县城发出求援的信件,七天后,阳安即将失守——
贾诩还让他等。
张绣坐不住了。
他倒没有急冲冲地去寻贾诩,当面质问,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叔父,半真半假地抱怨:
“贾文和什么都好,就是太喜欢故弄玄虚。每次向他问策,他都不说出个所以然,只告诉我要如何去做。
“譬如这回,曹操大军来势汹汹,我虚心地向他求教,他却只让我‘等’。等了一日又一日,等得阳安城都要失守了,他还让我‘等’。等等等,等他个阿翁。”
张济瞥了年少气胜的侄子一眼:“他与你说明前因后果,你就能懂了?”
叔父的话让张绣一噎,却还是犟着头:“那也总比一无所知强。”
“事以密成。何况,那些聪明人心中的弯弯绕绕不是我们能懂的。倘若他向你解释了一个甲,你又要询问乙;他向你解释了丙,你又要询问丁。问来问去,无穷无尽,哪还有其他事可做。”
这话让张绣答不上来,可他仍然有话要说:“叔父,你就真的这么相信这个贾诩?万一他是在毫无根据地胡说,害我们失了先机,陷入被动的局面,那可怎么办?”
“那就被动。”
张济为自己斟了一杯酒,一口饮尽,回味着口中的醇香,
“你可知董太师、王允、李傕郭汜为何守不住长安?”
望着张绣若有所思的侧脸,张济寓意深长地教导着唯一的子侄,
“不是因为他们缺兵少粮,更不是因为他们时运不济,而是因为他们身边没有得用的‘策士’,也不懂得分辨谏言,当自己是全天下最聪明的人。”
“这天下的奇才,多如牛毛,可这牛毛也分粗细。我们既然找到了其中最粗的一根,就该紧紧抓住,不要让牛毛折断,或是被风吹走。”
张济说得情真意切,丝毫没发觉自己的侄子露出古怪的神色,好似被他的形容呛了鼻。
贾诩那张平和内敛、胸有成竹的面孔在张绣的脑中浮现,慢慢长出牛耳朵与牛鼻子。而后,变成牛的贾诩从自己的屁股后方拽下最粗的一根毛,递到他眼前,粗声粗气地哞了一声:“抓紧了。”
张绣差点没因为这个遐思而笑场。他连忙板起面孔,静下心,恰巧听到了叔父的最后一句总结。
“西楚霸王何其强也,最终不过是一个败字。我不求在乱世中成就霸业,只愿能择一安身之地……”
张绣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惊疑不定地看向叔父:“叔父,你不会是要投靠那个曹操吧?”
“想哪去了。”张济嗔怪地摇头,“曹操不过侥幸得了一个兖州,哪里是什么值得投效的明主?就算以后不得已,不得不投靠曹操,那也是以后的事。”
张绣不由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段谈话,他对贾诩越发恭敬,哪怕阳安被破,汝南北部被曹仁连破三城,张绣也始终沉住气,不曾派兵支援。
到了第十五天,张绣终于知道贾诩让他等的是什么——
预谋夺下徐州,抢占龙气之地的袁术,因为“僭越称帝”“意图谋害天子”“谋逆不轨”等罪名,被破虏将军孙坚斩于马下。
孙坚杀死袁术,占据了他的势力,杀死了一些不服从他的人马,接着便率领大军撤出徐州,不再攻打陶谦。
他派遣使者来与张济求盟,为了表示诚意,还派来了自己的长子孙策。
孙策时年十七,相貌出众,武艺非凡。他还未及冠,言语处事却已颇具章法,让人不敢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