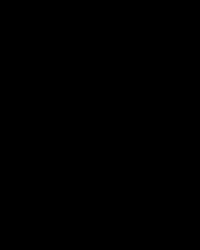阁笔趣>[三国]“病弱”谋士,战绩可查 > 150160(第19页)
150160(第19页)
张机收起脉枕,询问顾至:“你想让我‘一并看了’的亲友住在何处?”
顾至早已习惯张机的直来直往,摇头道:
“倒是不急于一时。仲景忙了半日,粒米未进,我已让人在家中备好饭食,等仲景休憩一番,用过饭食,再作安排。”
张机叹道:“堆着的事未做完,我总安不下心来,只想一口气将所有事理个清楚。”
顾至见过张机废寝忘食研究医术的模样,知晓他的脾性,不再多劝。
好在郭嘉与戏志才住得不远,顾至将他们几个聚在家中,让张机一一诊脉。
“荀侍中身轻体健,并无不妥,只仲夏阳气外浮,需得备好清热降暑的汤剂。”
“戏参军脉象起伏,似曾有不足之相。如今虽已康复,但也要多加注意,莫要劳累过度。”
当轮到郭嘉诊脉,张机反复切脉,沉目不语,所耗费的时间比前两人加起来都长。
想到郭嘉在原著中的寿数,顾至难免有些不安。
他极力忍耐着询问的念头,不去打扰张机的诊断,身为当事人的郭嘉却气定神闲地坐着,口无遮拦地发问。
“怎么了,张神医,莫非在下得了不治之症?”
“奉孝莫要胡说。”顾至蹙眉喝止,拔高的声量震得郭嘉不自觉地一滞。
郭嘉犹想说几句玩笑话,抬头一扫,顾至眼中夹着灼火的火苗,荀彧面上尽是不认同的神色,就连一向不愿搭理他的戏志才,都板着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立即闭上嘴,老老实实地坐着。
张机未曾关注身后的动静,只神色板正地与郭嘉对视。
“郭祭酒所罹患的并非不治之症,却比不治之症更加棘手。”
这话像是平空惊雷,让在场的人都提起心。哪怕是一直没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放心上的郭嘉,也忍不住坐直身子,引颈而望。
“此言何解?”
郭嘉想着自己往日无痛无灾,只比旁人多一些头痛脑热,实在难以相信张机的话。
可张机须发摇曳,正是德深望重的模样,又带着医者特有的严肃,让他不得不信。
“莫非我真的病得这般严重?”
“若只是不治之症,躺着等死便是。”
张机颔首,抚平颌下的长髯,
“郭祭酒年纪尚轻,又无膏肓之疾,若要郭祭酒‘躺着等死’,怕是要人人喊我一句庸医。”
向来医者仁心的他,弯起一道偏冷的笑意,
“可郭祭酒殚精劳神,过饮过食,久坐少眠,这三者对身体的弊害,无药可医。”
在场的都是脑子活络的人,自然听懂了张机的这段话。
一向不知局促为何物的郭嘉难得有些讪讪,在好友前后夹击的火热目光中,他轻咳了一声。
“听先生一言,如醍醐灌顶,还请先生教一教嘉,嘉一定改正。”
“郭祭酒言重。”张机收敛唇边的冷意,恢复最初的平和。
“只需郭祭酒明白,天有时序,物有节令,不可满亏。”
“多谢先生。”
张机给三人各开了养生的药方,最终将目光落在顾至的身上。
“来都来了,不妨一看?”
顾至早有准备,递上右手。
“如何?”
张机颔首道:“五气调和,六脉通畅。”
有一个时刻关注他饮食起居与身体健康的伴侣,想不通畅都不行。
顾至正想揪着郭嘉,让他明天开始与自己一起晨练,倏然,院门被人敲响,一位不速之客登门,竟是几日没有露面的祢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