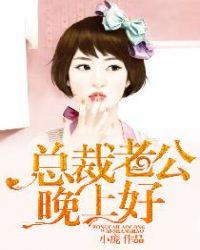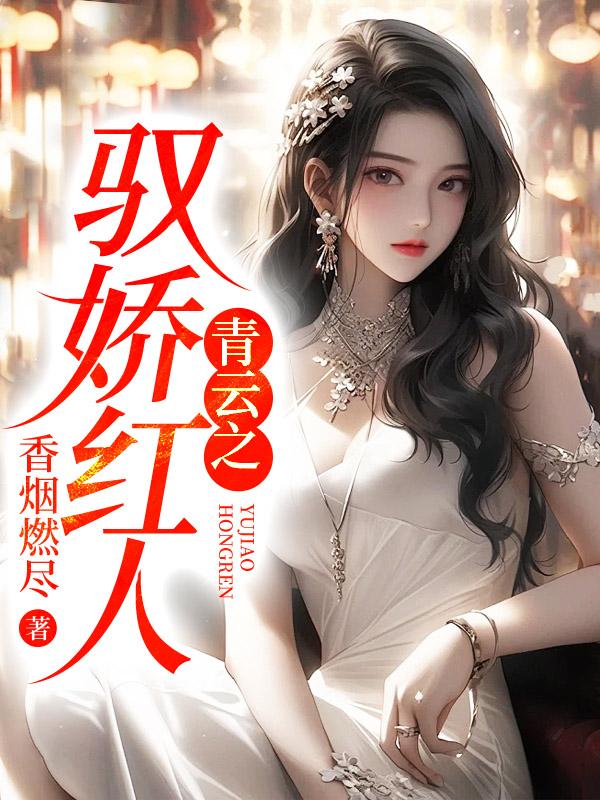阁笔趣>军户的填房甄珠全文免费阅读 > 第246章(第1页)
第246章(第1页)
待到出了右掖门,他们才浑身一松,开始放开地谈论起殿试的情况。“黄兄高见呀!我们怎么就想不到海禁能够达到清减官吏臃肿这个点呢!”“不愧是我们之中的春闱第一,这不妥妥的状元郎了。”“黄兄他朝高中,可莫忘了弟兄们哦。”“苟富贵,勿相忘!”……而陆杰修和秦朝宁没过多讨论殿试的事,也没上前去凑同年们的热闹。他们互相祝对方高中,就各自走向自家的马车归家去了。后续,殿试的所有答卷在外帘官们弥封、誊写后,就转送给了内帘官们。殿试的内帘官也是翰林院的官员抽调为主,只是最后一道评卷人是内阁几位阁老。他们会决定殿试的排名,列好名单。这之后,内阁呈上对应新科进士的答卷,再由圣上裁夺最终结果。正历十年殿试后的第三天,翰林们已经挑选出了二十份卷子出来,等待阁老们的点评。整整二十份答卷,眼下都铺在内阁的长案桌上,首辅、次首辅,五名阁老皆到场。而阅卷的翰林们均站立在阁老们的身后,以便阁老们稍后提问,抽查他们的阅卷和提名情况。以杨首辅为首的阁老们,逐一把答卷看过去。他们这会儿看到的答卷已经是原卷,非弥封誊写卷。所以,每一个新科进士的字迹、文章想法,对于他们来说,都一目了然。先是字如其人,从字就能看得出来该学子的几分心性。紧接着,文章里的典故,语句能够看出该学子的才学程度。最重要的是,文章里的想法,就是该学子的里子。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这个人在未来朝堂上,是否会成为己方的一员。只有信念相同、目标相近的人,才会在朝堂上的方方面面达到一股合力,去推动己方想要看到的结果,争取到符合己方的资源和利益。几刻钟后,所有阁老都把案桌上这二十份答卷看完了。于是,杨首辅发话道,“既然所有答卷都看过,各位大人便把自己心中的排名写到纸上吧。”“内阁老规矩。”闻言,次首辅汪阁老笑了笑,表明立场,“如此甚好,各位同僚也放心写吧。”他又补充了一句,“最后还有圣上定夺呢,咱们就随心。”这一句是提醒,该怎么意会就是在场各人的事。一会儿后,七份名单就出来了。这几份名单里,大部分排名是一致的。什么水平排在什么名次,在场的阁老们水平相当,想法也类似。唯一有分歧的是春闱排名第一的黄致远,排名第二的陆杰修,排名第三的秦朝宁。七份名单里面,把黄致远写在第一的有三份,即三票,其余票则是普遍在前十内。陆杰修则是获得了第二的三票,第八的四票。而秦朝宁排第一的一票,其余六票是排在第二十。这相当于是在场的阁老们对此争议甚大。并且,从名单上的字迹一看,众人都认得出来,那一份把秦朝宁写了第一名的名单,是出自刘阁老的手。杨首辅一副老好人的笑容,调侃刘旭道,“刘阁老倒是举贤不避亲,坦荡得让本官佩服。”他的话语里,点出刘阁老和秦朝宁的座师门生关系,以及给扣上了,刘旭是否存在吃相难看的帽子。刘旭面上的脾性也是好得很,闻言淡笑道,“本官不过遵从内心觉得该文章值得一个上等。”甭管他有没有听出来杨首辅的意有所指,秦朝宁的开海建议,他愿意一信。他私心讨厌治标不治本的高谈阔论。黄致远在他的名单里排第九,而同样希望从改革出发的陆杰修,他是写的第二名。状元郎内阁的意见难以统一,最后便是抓阄定的名次。抓阄也是内阁的老传统了,并非儿戏。实在是,聪明人太多,往常针对政事能够想出来的解决法子虽各有不同,却也大差不差。那么,若是意见不决,便抓阄吧,抓中了哪个便用哪个的法子。这样也可以避开许多明面上的摩擦。斗争可以,但是都能做到阁老的人了,分寸要顾忌着。谁的底下、门下,不是一串一串的学生、子嗣、旁支的。做人留一线,都是给身后那些小辈留的余地。除非,能一锅端了对方,不留后患,要不然,众人还是会愿意维持面上的那张纸不捅破。内阁最终呈上给历帝的名单,殿试第一名是黄致远,陆杰修是排在第八名,秦朝宁是在第十二名。等在圣乾宫的历帝,从总管太监周伯通手里接过了名单,他把该名单从上到下看着。越看,他的双眸就越深邃。周伯通,已是花甲之年,是在历帝自幼就贴身照顾历帝长大的内侍。如今,他是四品的宫殿监督领侍,总管太监中的一员。这会儿,周伯通半弯着腰,把内阁送过来前二十的新科进士答卷放置在桌侧,笑着提醒历帝,“圣上都处理了一上午的公务了,何不先歇息片刻,吃过御膳后再看。”“阿公,稍后”,历帝对着名单轻轻蹙了眉,右手在桌上叩了叩。这是历帝沉思时候的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