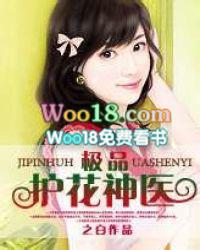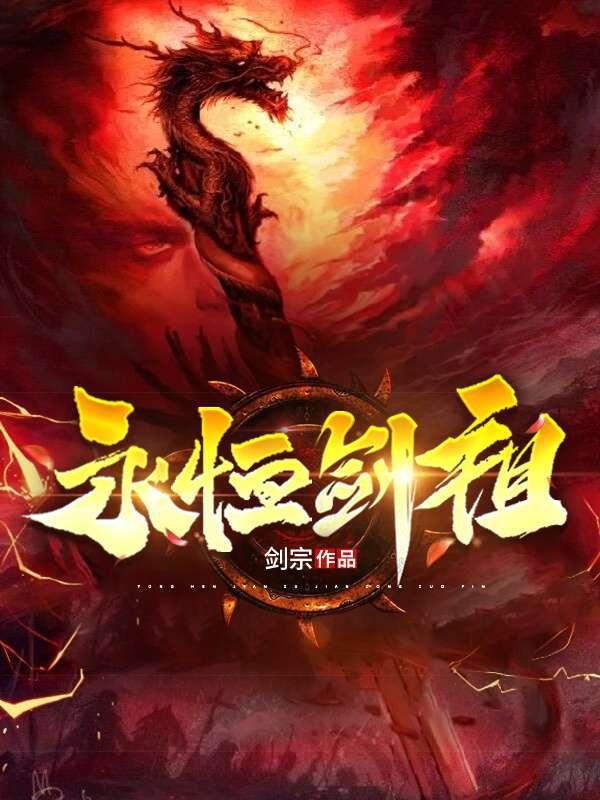阁笔趣>剑宗外门 > 第375章 魔临(第1页)
第375章 魔临(第1页)
广陵府,绘山。
这一片山脉,本非灵脉汇聚之地,山势险峻荒芜,人迹罕至。
山阴之地,一座庞大的阵台,其上阵纹繁复,隐隐流转着幽暗光芒。
那些幽光正徐徐而起,将四周的灵气斥开。
古。。。
夜色如墨,浸透了长崎港的礁石与桅杆。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息,在庙宇残垣间穿行,吹动檐角铜铃,一声轻响,仿佛回应三年前那场跨越重洋的呼唤。李念站在归航的船头,手中紧握一枚信笺??是岭南分坊急递而来的新消息:柳含章虽伏法,其“再造民心”计划却已在江南数府悄然推行,三百余种民间抄本被焚,数十名私授《全史》的塾师遭拘,更有孩童因背诵《悔过席》而被逐出学堂。
她闭目良久,指尖抚过衣襟内侧藏着的南宫氏铜铃。铃声未再响起,但那一夜《照心引》的余音,仍如细针扎在心头。
船抵言城外码头时,天光初露。陈七早已候在岸边,蓑衣湿透,脸色凝重。“他们改了科举章程。”他低声道,“今岁秋闱,新增‘史鉴’一科,考题皆出自官修《贞元实录》,凡有引用野史者,一律黜落。礼部已下令,各州县设立‘正史讲堂’,专授钦定文本。”
李念默然踏上青石阶,脚底泥泞黏连,一如十年前初回此地的模样。无名堂门前槐树依旧,只是枝干上多了几道刀刻痕迹,隐约可见“真”“灯”二字。推门而入,堂中灯火通明,十余名校书生正伏案疾书,墙上挂着一幅新绘地图,红线密布,标注着全国三十六处“焚书点”。
“这不是第一次。”一位老校工抬头,声音沙哑,“先帝年间,也曾烧过一次书。那时我在国子监做杂役,亲眼见太学生们抱着残卷跳进火堆,用身体压住火焰,说‘只要还有一页纸活着,历史就不算死’。”
李念缓缓解下斗篷,从竹篓中取出一只檀木匣。匣内层层油纸包裹,最里层是一卷泛黄绢帛??正是《海外贞元录》初稿,附有十七位流亡士人后裔亲笔签名作证。她将其置于案首,轻声道:“那就再点一次灯。”
当夜,无名堂地下密室开启。这里原是传灯会藏匿禁书之地,如今扩建成刻坊,藏板三百余副,日夜轮转印制《全史》补遗。李念召集骨干议事,宣布启动“破镜行动”:以商队、僧侣、走方郎中为线,将新版《全史》混入药材包、佛经箱、嫁妆盒,送往各地私塾与书院;同时派遣游学先生伪装成算命瞎子、卖唱女伶,口传心授《异闻录》片段,务使真相如根须般钻入每一寸冻土。
“我们不再等他们允许说话。”她说,“我们要让每一个不能读的人听见,让每一个不敢写的人记住。”
行动甫启,阻力即至。半月之内,三批运书商队遭劫,两名联络人暴毙街头,尸体旁留有黑羽箭,箭尾刻着“影阁旧印”。朝廷虽已废除影阁之名,然暗流未息,新设“清源司”代行其职,手段更酷烈。某日清晨,照心碑前竟出现一具无头尸,身披学士袍,胸口钉着一张纸条:“说谎者,无面见祖宗。”
人心惶惶之际,李念却做出惊人之举??她公开现身城南大市,立台讲史。
那天正值寒食节,百姓扫墓归来,聚于集市。她在茶棚搭起高台,不请官绅,不邀文士,只对贩夫走卒、村妇农夫开口:
“诸位可知,三十年前,有个叫李慎的大将军,不是病死的?他是被人毒死的。就因为他主张开仓赈灾,不让百姓饿死,所以皇帝身边的权臣怕他得民心,就在酒里下了药。”
人群骚动。有人冷笑,有人掩耳欲去,更多人驻足倾听。
“又有个叫南宫萤的先生,写了十万字奏疏揭发弊政,结果被说成妖言惑众,全家流放。他临走前说:‘真正的忠臣,不是为君死节,而是为民存真。’这话你们觉得对不对?”
一个卖菜老妪颤声问:“那……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
李念望向远方碑林,答:“有。就在你们中间。每一个不肯忘记的人,都是。”
讲至深夜,台下聚集数百人。有人掏出随身携带的桑皮纸,求她写下李慎遗言;有个盲童跪地磕头,请教《悔过席》全文。李念一一应允,命人当场誊抄百份,分发众人。
此事震动朝野。三日后,圣旨下达:责令地方严查“聚众妄言”之徒。可讽刺的是,就在诏令张贴当日,京城三大书院联合发布《护史约》,声明“凡禁书所载,若能证其属实,则非悖逆,乃补阙也”,并宣布将在每月初五举办“自由讲史日”。
民间响应如潮。短短一月,全国兴起“夜读会”千余处,多设于祠堂、碾坊、渡口,参与者不分贵贱,皆以烛火为誓,轮流朗读《全史》。有村妇边纺线边背诵南宫萤奏疏,有铁匠趁打铁间隙高声复述沈无咎供词,火星四溅中,字字铿锵。
而最令人动容者,莫过于岭南某山村小学。九名学童在老师带领下,每日放学后集体抄写《归音录》,每人负责一段,完成后埋入校舍地基之下,立石为记:“待百年后掘出,可知今日吾辈未敢忘。”
李念得知,泪流满面。
然而风暴仍在酝酿。清源司首领竟是柳含章胞弟柳承业,此人阴鸷胜兄,竟想出一毒计:伪造李念手书,捏造其勾结扶桑幕府、意图引倭寇入侵之“铁证”,并暗中资助江湖术士散布谶语:“黑衣女子现,天下兵戈起。”
一时之间,舆论倒戈。百姓恐惧战乱,纷纷交出私藏书籍以示忠诚。连原本支持她的崔衍也被迫上表自辩,称“曾受蒙蔽,今后必严守正统”。
危局之中,一道身影悄然现身无名堂。
来人紫袍玉带,面白无须,正是宫中掌管图书典籍的内侍监周德全。他曾是裴文渊亲信,亦参与当年焚毁南宫府藏书之事。十年前,他在一场大火中救出半卷《贞元起居注》残篇,藏于佛像腹中,此后常年斋戒诵经,似有所悔。
“李姑娘,”他双手奉上一只鎏金小盒,“这是我欠下的债。”
盒中是一枚象牙签牌,刻有“贞元十三年十二月初七内廷密录”字样,背面赫然写着:“戌时三刻,枢密使裴某携药入御膳房,亲监煮酒。李相归邸后暴卒,上赐白绫十匹、黄金百两予裴。”
这是迄今为止最直接的宫廷记录!不仅证实李慎之死系裴文渊亲手操办,更揭示皇帝知情且嘉奖凶手!
“为何现在才给?”李念盯着他。
周德全垂首:“因为我一直不信有人能坚持到今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在某一天停下。可你没有。你让一个罪人看见了光??哪怕这光照见的是自己的黑暗。”
他离去时脚步踉跄,仿佛卸下千斤重担。
凭借这份证据,李念再度掀起巨浪。她将签牌拓印百份,附以考证文章,命名为《内廷血契》,秘密送往各国使节及地方大员。同时发动“万人联署”,邀请所有愿为真相作证者签名按印,誓言“宁受株连,不弃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