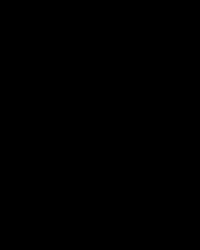阁笔趣>如何溺毙一只鹤 > 第一百二十四章 白云苍狗(第1页)
第一百二十四章 白云苍狗(第1页)
纪年看见纪辰身后攥得紧紧的拳头,手背上青筋凸起,微不可查地颤抖着。
“沈、侧、妃明察,我只是说了些该说的话。”纪辰格外加重了那个“侧”字,而后挑起眼神,藐视着沈莺扑着白粉的脸。
“早就看你这个狗崽子不爽,什么下贱东西,起了个与我孩儿相近的名,居然真以为自己也尊贵了。”
沈莺对纪辰的恼怒颇有些强词夺理,这事人尽皆知,只因为纪辰的“辰”字与纪城的“城”字读音相像,便惹得沈莺不爽已久。她曾向平亲王不止一次提及过要给纪辰改名,让她的儿子避一避晦气,不知道的还以为纪辰的名字会让纪城的眼睛变成紫色。
可能是平亲王嫌烦,也可能是他根本忘了还有纪辰这个名字,毕竟他更愿意称呼自己的二儿子为“脏了血脉的贱货”,所以直到现在纪辰的名字也没有改成。
“来人,”沈莺朝着身后的仆从一挥手,“拉下去,就由我替他那死人母亲教育他。”
几个彪壮的大汉挤进学宫里,三两下蹿到纪辰桌前,推搡他往外走。
场面一片混乱,夫子碍于沈莺只得噤声,余下的学子更是不敢出声。
纪城徒劳地挥动双手,被沈莺一剂眼刀吓得缩回了手。纪年立即伸手抱住纪辰的腿,想要大喊求饶。但纪辰浅浅看了他一眼,示意他放手。
纪年懊丧地把手缩回去,整个人缩回自己的位置上,眼睁睁看着纪辰消失在视线中。沈莺趾高气昂地随人群出去,身后跟着快要哭出来的纪城。纪然站在人群之外,满意地观望这场闹剧。
平亲王府真是个好不公的地方。纪年想。
此后纪辰那院里一直没见人出来,纪年和母亲哭了一通,可他母亲亦不敢触了沈莺的霉头。等到纪年再见他哥哥已是一旬之后,他下了被沈莺打死的决心,翻过院墙进去。
纪辰在树下读书。他毕竟是皇家子弟,沈莺也不敢真打死他。纪年只见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尤其是眼周,斑驳得不成样子。
纪年站定,双手紧紧攥住衣角,目光绕过他哥哥浑身,然后眼睛越来越红,眼眶里有水光在打转,最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纪辰显得有些局促,也站起身来,道:“你哭什么。”
“是、是我的错。。。。。。”纪年啜泣着擦眼泪,“若不是我非要让你来陪我,就不会找到三哥,也不会。。。。。。也不会。。。。。。”
纪辰无奈地笑笑,又不小心扯到脸上的伤,轻轻嘶声。他走过去把纪年抱进怀里,安慰道:“不是你和纪城惊动了沈莺,而是世子命人去给沈莺报了信。”
“可是,可是你与世子无冤无仇。。。。。。”
“纪然厌恶他每一个弟弟,在他眼里,所有纪姓男子都是对他世子位的威胁。他嘲讽我,是因为他一不敢招惹沈莺,二不想与你一个几岁的孩子纠缠。他见我无趣,又不想让纪城顺心,便叫了沈莺来。我不让你与沈莺争执,不是说争执没用,而是害怕我若躲过去,挨下这些的只会是我的母亲。”
“不是的。。。。。。平日里他根本不会注意你,都是我的错。。。。。。”
纪辰在他背后拍了一下,正色道:“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欢自怨自艾者,说了不怪你就是不怪你,不必多言。我长成这样是天意,是命中注定这幅模样,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凭什么。”纪年泪眼婆娑地抬起头问道,“阿辰哥哥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纪辰怔住了。
“你不应该、不该被他们这样。。。。。。”纪年哭得咳喘,“他们不能这样对你。。。。。。凭什么。”
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他只是走他自己的路,只是活着。
他的人生若是一片旷野,那他的兄弟便是灼烧他的火难,他的父亲是助长火势的狂风,他的母亲是于火焰中自身难保的溪水。
在这里仅仅因为一双眼睛,便能把一个人深深埋进土里,肆意践踏,任人凌辱。
“沈莺可能已然盯上你了。虽说你的母亲出身贾氏,”纪辰最终缓缓道,“我不会出事的,你以后切莫再来了。”
纪年使出浑身力气摇头,把眼泪全甩在他哥哥身上。
“我只是你一个玩伴,并不是你独一无二的谁。你身边以后还会有很多人,没了我你不会感到孤独。”
“但是。。。。。。”
“我并非好为人师。”纪辰郑重道,“但我不会害你。我不会的,小年。”
但是你会孤独。
纪年的岁数还是太小了,并不能很好明白这“孤独”的含义。
可“孤独”与“一个人”的意思并非相同。纪辰所言的孤独宛如静寂的夜,无论何人怒吼嘶喊又嚎叫痛哭,都只能听见星落无声。
纪年抬起头,看见那双紫色的眼睛。
这双眼眸有如银河翻涌,夜色倒映其中,瑰丽,凝重,又浩浩汤汤。
————
纪年是个很听话的孩子,这是他在平亲王府得宠的法宝。他最听的是母亲的话,其次便是他阿辰哥哥的。纪辰不让他去他便不去,院子里只属于他们的午后变成了在学宫里多看他一眼。
在王府的日子平静而安宁,春去暑往,秋过冬来,转眼便是天乾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