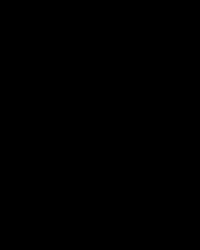阁笔趣>如何溺毙一只鹤 > 第一百六十六章 悬而未决(第1页)
第一百六十六章 悬而未决(第1页)
红玛瑙耳饰应声滚落,甩至一处角落。贺言大口喘息着,纪清的脸被扇往一侧。
“你上次和我动手是当年在云平城外,我阻拦你给你父亲收尸。”纪清捂着脸正过身子,“这是第二次,为了你大哥。”
十三岁开始尖叫,像厉风经过枯木,鬼怪咆哮。十五岁跪在他脚边,哀嚎着让他闭嘴。康武元年在静静地哭。他们很吵,吵得纪清有些想吐。
“我权当你气昏了头,说的都是浑话。”贺言后撤两步,哑着嗓子说,“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我说了什么,我清清楚楚。”纪清脸颊疼得发辣,他把指甲掐进手心里。
“你始终喜欢明丽的女子。同我相拥会让你恶心吗?与我齐名时你会不甘吗?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委屈你了。”
纪清的面容有些狰狞,双眼写满了“绝望”二字,宛如绷紧的琴弦,每说一个字就离断裂近一分。
“我不欠你了。”他硬生生笑出声来,“贺言,这些年你受苦了。”
那双对他笑过哭过,见过春荣秋枯和云卷云舒,目睹尸山血海与天上人间的双眸,无助地看过来,看向他。
十三岁耀武扬威地放声大叫,剩下的两个烂泥一般瘫在他脚边。
不该这么说的。纪清想。绝不该,万不该。
贺言其实是个挺无坚不摧的人。
施南骂他猫嫌狗厌颇不要脸,朽木无以雕烂泥不上墙,他把头埋进话本里两耳不闻圣前书,你骂你的我玩我的,既然两相生厌那就别对视了。
贺柏把他打到乱窜,比过年放的窜天猴还高,上能上树下可进水,夏翎在一边鼓掌叫好,表弟你真厉害飞得真高。当时甚至有这么一个说法:贺府门口三天坐,梨园台上无名角。他爹颇害臊,他颇得意。
后来夏淑棋死了,他咬着牙推演出了计划,纪辰的性命开始倒计时。此后死亡胜过泼皮无赖,占据了他人生的最大一部分,他自己的亲人,无辜的路人,和最终了结的敌人。
写在黄历上的祭日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他告诉自己:日子还长,天地有眼,善恶有报。
这之后兰图哈木的信送来,大火把他烧得几乎一干二净。
说实话他不愿意挨打,没人愿意挨打。疼是真的,冤也是真的。在西六街他连女子的衣角都没碰过,只盯着木槿一个人的胳膊。逃学就往静宁殿跑,哪来得及清闲?
他演给雁城的看客,演给贺柏,演给夏翎与莫项,演给纪洵川,最后也演给他自己。
那些伤疤被细细吻过时,他战栗,惊惶,不过即刻在欲海中来不及顾及过往的痛苦。这人也是他的观众,只不过是第一个让他甘愿走下戏台的观众。
可惜又幸好,一切都是真的。计划是,谎言是,爱也是。
“。。。。。。是,你说得对。”贺言点点头,“我受苦了。”
这是他无所不尽其极保护的人,亲口对他说的话。
这是那个阴翳变态的小皇子能说出来的话。
贺言带着被草草止了血的伤口回到家中时这么称呼过他,后来删了“阴翳变态”这个限制,只剩下“小皇子”。时过境迁变成“纪清”和“纪洵川”,直到贺镜目瞪口呆地发现他俩私会,便拿“你家王爷”调侃。
有些人是向往真相的,哪怕真相将毁掉一切。纪清赫然位于其间,找到了他为他营造的温柔乡的边界。他没法与纪清共情,如此激烈的欺骗他没尝过,不配品评。
但是,他始终是个积极的人,不然人生这么苦他早就上吊了。诚然,不是现在。
贺言扭头便走,只留下一个颤抖的背影。
他比去年更瘦了,大氅挂在肩上,显得更为单薄。束发的雕花银环昨夜被烧得发黑,还未来得及换。他浑身连一件像样的配饰也没有,匆匆忙忙过来见一面,本意是扑进爱人怀里诉苦。